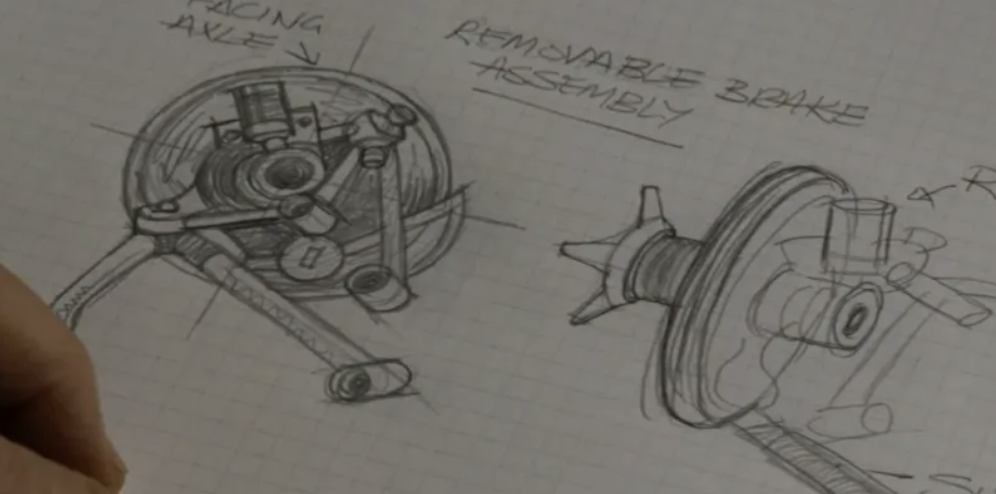特斯拉今年三季报略显平庸,但画饼仙人马斯克成功完成电话会逆转。凭借业绩指引和Model 2两张大饼,资本市场喜笑颜开,给特斯拉送上大涨。
大超预期的汽车毛利率和提前释放的交付量指引,构成了资本市场用钱投票的核心因素,但这绝对不是马斯克乐见的景象。
2022年开始,马斯克就在各种场合积极吹风,不断剥离特斯拉“汽车生产商”的身份,用“人工智能”元素取而代之。具体话术包括但不限于“如果你把特斯拉只看作一家汽车公司,那么你对特斯拉的理解就是片面的”、“如果特斯拉只是个电动车公司,它就完了”等等。
今年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马斯克在不到60分钟的时间里,蹦出28次“AI”一词 ,平均两分钟一次。
算上一季度电话会,马斯克一共提及43次AI,相当于去年四个季度的总和、2022年的2倍多、2021年的6倍多。
把财报电话会的关键词分为两类,一类是汽车生产相关(automotive、factory、capacity),一类是人工智能相关(self-driving/autonomous、AI、robot),那么过去22个季度的电话会,前者的露脸频率在持续下滑,后者则极速提高。

2022年之前,马斯克明显更关心汽车生产,“AI”作为一个单词,出现频率还不如Shanghai的最后两个字母。
到了今年二季度的电话会,“AI系”词汇的出现频率已经达到了“制造系”的近8倍。马斯克在电话会上说[1],“我们已开始踏上公司迈向下一阶段的征程,基础工作已准备就绪。”
马斯克对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改造”人尽皆知,过去数年,特斯拉积累了一个由端到端算法、FSD自动驾驶芯片和云端Dojo算力组成的AI系统。马斯克本人不仅是OpenAI的创始人之一,他参与的人工智能项目还有脑机芯片Neuralink、聊天机器人Grok等等。
或高调或沉稳的布局背后,是马斯克为特斯拉勾勒的一条清晰的转型战略:
以美国的优势产业为基石,重新构建特斯拉的竞争力。
上海工厂的奇迹
《马斯克传》的扉页上,马斯克本人写了这么一段话:
“对于所有曾被我冒犯的人,我只想对你们说,我重新发明了电动车,我要用火箭飞船把人类送上火星。我要是个冷静、随和的普通人,你们觉得我还能做到这些吗?”
此话不假,只不过在多次中国之行中,马斯克不仅冷静随和,面对各色政府官员也游刃有余,完全不像一个聊天聊到动情时会抽大麻的企业家。
中国是特斯拉成长史上绕不开的章节。2018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达到125.6万辆[3],占全球总体的六成以上。而特斯拉同期在中国注册量仅为13456辆,这是上海临港工厂建设最直接的动力。
作为特斯拉第一座海外工厂,上海工厂2019年1月开工,12月交付,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生产,当年交付”的制造业奇迹,让刚经历完Model 3产能地狱的马斯克,直观体会了工业克苏鲁的震撼力。
伴随上海工厂产能爬坡,特斯拉逐渐与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捆绑。2020年,上海工厂交付量达到14.9万辆,占特斯拉总产能的29.8%——2021年后,这个数字再也没有低于过50%。
相比之下,无论是根正苗红的弗里蒙特工厂,还是遥远的柏林工厂,都处于产能爬坡阶段。
目前,上海工厂是目前特斯拉所有工厂里,唯一一个达到了规划产能的超级工厂。
马斯克一度想在德国、墨西哥效仿上海模式,结果前者建厂进度条长达两年半,工厂建好了又遇到招工难;后者因为大选叫停了建厂进程,2026年的投产目标,眼看着又要往后顺延。
上海工厂强大的生产效率拯救了特斯拉,但这不是特斯拉的优势,而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
依托电动化迅速成长起来的供应链,中国车企开始迅速向电动化转型。截至去年底,全国398家整车厂中,有278家设有新能源产线。中国新势力破产是因为车卖不出去,美国新势力破产是因为车造不出来。
中国的新能源车的生产制造能力常被贴上“低成本优势”的标签,但事实并非如此。
电动车系统性创造了一些新的零部件,也系统性消灭了一些旧的零部件,在这个过程中,汽车供应链森严有序的格局被打破了。
丰田普锐斯唯一的目的是省油,但特斯拉彻底改变了汽车的架构和生产方式,并引入了动力电池、碳化硅MOSFET、高算力芯片等零部件,以及一体化压铸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上游供应链的结构,让小供应商咸鱼翻身成了可能。
同时,汽车是一个高度依赖本地供应链的产业,需求在哪里,供应链一定会转移到哪里。
福耀玻璃当年在美国建厂的原因被归结为美国的土地与能源成本更低,当然也有“不用给领导送礼”这种脑回路清奇的解读。但真实原因只有一个:玻璃运输难度太大,必须围绕整车组装厂就近建厂。
福耀在国内的制造基地都是为了配套附近的整车厂,其上汽工厂位于上海嘉定,隔壁就是大众的配件仓库。松下为特斯拉生产电池的工厂,甚至直接建在弗里蒙特工厂旁边。
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正式超过50%,作为对比,全球范围内的渗透率只有17%(Canalys口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供应商开始成建制地跻身产业链。
松下原本是特斯拉的独家电池供应商,由于对特斯拉的盈利不抱希望,松下放弃了跟特斯拉来中国建厂的计划,把这块大蛋糕让给了宁德时代和LG。
制造业用规模分摊成本的终极法则百年来不曾改变,中国供应链配套能力强、需求响应及时的鲜明优势,与供应网络错综复杂、零部件数以万计的汽车制造完美契合。
中国政府持续多年的产业补贴,收获的最大战利品不是早高峰一望无际的绿牌,而是一个完整的新能源车产业链和与之对应的生产制造能力。
今年10月Robotaxi发布当天,上海工厂下线第300万辆整车,其中超过100万辆用作出口。隔壁车间的Cybertruck仍在产能爬坡,按当前的产能计算,不少车主提车得等上五年。
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上,分析师对特斯拉的制造能力提出质疑,一向人狠话多的马斯克顾左右言他,称特斯拉应该被视为一家AI或机器人公司:“把特斯拉看做一家汽车公司,是完全错误的框架。”
消失的电池日
美国大选结束,马斯克顺利成为“第一兄弟”,特斯拉股价也一路走高。按照目前1.4万亿美元的估值计算,特斯拉的市值占全球汽车制造业近一半,超过了身后29家汽车生产商的总和。
如何给特斯拉估值,是华尔街的资本大鳄过去几年面临的最复杂最深奥的问题,多空双方带着真金白银发生过多轮大规模交火。
在漫长的博弈过程中,资本市场逐渐接受特斯拉不仅是一家汽车生产商,同时也是一家软件公司或人工智能公司。特斯拉头号铁粉“木头姐”Cathie Wood亲自构建了一套扎实的理论框架:
特斯拉是一家“移动即服务(MaaS) 公司”。所谓Maas服务,即特斯拉围绕自动驾驶算法构建的软件业务,包括FSD的订阅、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等等。
木头姐(右)与马斯克
除了资本市场的考量,特斯拉高举人工智能大旗还有更加现实的因素:特斯拉的生产制造能力,已经无法形成竞争优势。
2020年,特斯拉举办了第一届也是迄今唯一一届“电池日”,马斯克在现场摊了两张大饼:一是自产4680电池,降低电池成本;二是在三年内推出一款25000美元(约合17.8万人民币)的廉价车型。
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在马斯克看来,只有有效压缩动力电池的成本,才能为廉价车型的推出打好基础。
2020年的特斯拉电池日
工艺复杂、量产难度极高的4680电池,完美贴合了马斯克解决成本问题的思路,即“用成本最高的方法降低成本”:十个会计需要花一个月算好的账,马斯克会五十个程序员编写一套程序,把算账流程自动化,并且一天就能算完。
然而,电池日堪称马斯克画饼生涯的最大污点。
4680电池一波三折,最终超时半年顺利量产。但大洋彼岸,勤劳勇敢的东亚人民已经把动力电池单价打到了0.4元/Wh。也就是说,虽然4680电池本身获得了成功,但并未达到“成本比供应商低”的预设目标。
Model 2被赋予延续特斯拉整车故事的重任,却活成了“消失的它”,甚至没拥有过哪怕一页PPT。反而是同样价格区间里的“中国版Model 2”琳琅满目,在价格战的硝烟里杀的你死我活。
从电池日的悄悄退场,到AI Day走上台前,马斯克对汽车生产的事业心有序熄火,对软件和AI业务愈发上心。
特斯拉去年年底发布的V12版本算法,用一张打包一切的神经网络,终结了自动驾驶程序员被corner case绑架的一生,几个月后,马斯克飞往中国快闪24小时,激动得高盛连夜开启终局思维,为其预定了2030年750亿美元的收入。
看似最不靠谱的特斯拉机器人,也被马斯克贴上了“超过特斯拉其他业务总和”的标签,Model 2画饼4年,最终沦为Robotaxi发布会上一闪而过的龙套。
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斯克创办的人工智能公司xAI。公司在2023年3月创立,7月公开,11月发布首个大模型Grok,今年6月,xAI宣布建造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
122天后,由10万张H100构建的Colossus训练集群拔地而起,超过谷歌和OpenAI数据中心规模。正在建设的Cortex AI集群,规模是5万张H100+2万张特斯拉自研Dojo。
xAI团队庆祝Colossus建成
这样的效率神话恐怕只有五年前的上海超级工厂可以同日而语。只不过一座在西,一座在东,跨洋相望。
根据流传出的规划,xAI数据中心的算力很大一部分将被“输送”到特斯拉的弗里蒙特工厂和奥斯汀工厂,前者是S3XY四大车型的量产地,后者肩负着Cybertruck和4680电池的产能爬坡,算力则用于FSD和机器人的算法训练。
伴随一系列基于人工智能的软硬件成果陆续落地,特斯拉以AI构建竞争力的路线图也逐渐清晰。
上一个依托中国生产制造能力崛起,但把高附加值环节都存放在美国的公司是谁?没错,是苹果。
中国供应商生产了苹果90%以上的产品,但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产品规划到设计方案,全部在位于加州的苹果总部中完成。就像苹果包装盒上印着的那句话一样: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掌舵者,马斯克显然比谁都清楚,特斯拉的护城河应该在哪挖。
美国公司特斯拉
2021年特斯拉AI Day,马斯克身边前所未有的拥挤,自动驾驶算法、FSD芯片和Dojo超算背后的全明星阵容第一次公开亮相。
会场上,特斯拉软硬件部门发量浓密的工程师在“总忽悠师”身旁一字排开,他们分别是:AI总监Andrej Karpathy、Dojo超算负责人Ganesh Venkataramanan、Autopilot总监Ashok Elluswamy、工程总监Milan Kovac。
这是特斯拉2016年开始组建各个软硬件部门后,固定下来的领导班子,也是特斯拉人工智能帝国的开国元勋。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应该是Andrej Karpathy,这位小哥的导师从李飞飞,与吴恩达合写过论文,不到30岁已经名满学术圈。毕业后,Andrej Karpathy参与创办OpenAI,2017年被马斯克厚着脸皮挖到了特斯拉,直接向自己汇报。
芯片大神Jim Keller是合影中的重大缺席者,作为硅谷顶级芯片架构师,Jim Keller的成名作包括AMD Athlon、Apple Silicon开山之作A4、AMD Zen架构等等。在特斯拉,Jim Keller主导开发了FSD自动驾驶芯片。
Jim Keller(左)
换句话说,马斯克第一次打芯片的仗,已经富裕得够正经芯片公司打一辈子了。
时至今日,这些人大多已经离开了特斯拉,比如Jim Keller去英特尔补了一段时间锅,随后下海创业。Andrej Karpathy后来回归OpenAI,Venkataramanan也在2023年离职。面对得力干将轮番离职,马斯克在一次采访中说[11]:“人家随便去哪儿都能找到工作,没有谁是他们真正的老板。”
但更接近事实的原因恐怕是:每一个功成身退的大师身后,总有一个替补队员时刻待命。
Jim Keller离职后,他在苹果的前同事Pete Bannon接管芯片设计团队。Karpathy离职后,四人组中的Ashok Elluswamy、Milan Kovac开始领导AI部门。
看似频繁的人才流动,恰恰是支撑特斯拉向人工智能转型的核心因素:美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计算机科学人才。
虽然关于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讨论不绝于耳,但以软件为核心的计算机科学这门产业,不仅从未“外流”到其他经济体,反而优势越来越大。从晶体管、集成电路,到Unix、x86架构,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美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几乎都是领跑者的角色。
顶尖的人才总是会向产业的高地流动,在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消费电子等产业,金字塔尖林立的巨头几乎都是美国公司。这些产业不仅吸引着全球最顶级的人才,也在为前沿技术不断培养着人才预备役。
特斯拉崛起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微软、Google、AMD这些IT巨头源源不断的人才输送,他们是制造业的门外汉,但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一骑绝尘。
中国在自身的优势产业里,也在体现出这种“产业厚度优势”。宁德时代的拔地而起和欧洲电池公司Northvolt的仓促退场,区别不在成本,而在于人才的供给。
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出现前,消费电子产品的锂电池就早早在东亚地区落地生根,曾毓群的老东家ATL就是iPod的电池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电化学人才会跟随产业链的转移流动,为动力电池的发展提供了相当可观的人才供给。
Northvolt的高管团队中,电化学背景的人才寥寥无几,欧洲的电化学人才储备同样一片荒芜。原因不难理解,上一个全球知名的欧洲消费电子品牌是谁?很可能是诺基亚。
全球分工的熔炉中,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会自发地找到应许之地。
欧洲汽车工业的繁荣,是因为斯柯达和克虏伯在100年前就开始做大炮了;特斯拉诞生前,汽车工业是美国铁锈带最显眼的伤疤;中国的汽车生产商恐怕不懂通用人工智能,但在生产制造上可谓德艺双馨。
国力的竞争是产业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在电动车智能化提速时,特斯拉希望用自动驾驶算法、Robotaxi和机器人构建一个人工智能帝国;而中国的新势力也在拼命补课,试图补齐自身在芯片、软件等环节的短板。
一个科技大国试图重现制造业的荣光,一个制造业强国从未如此接近自己在汽车工业领域的雄心,这会是21世纪商业史上最壮丽的章节。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